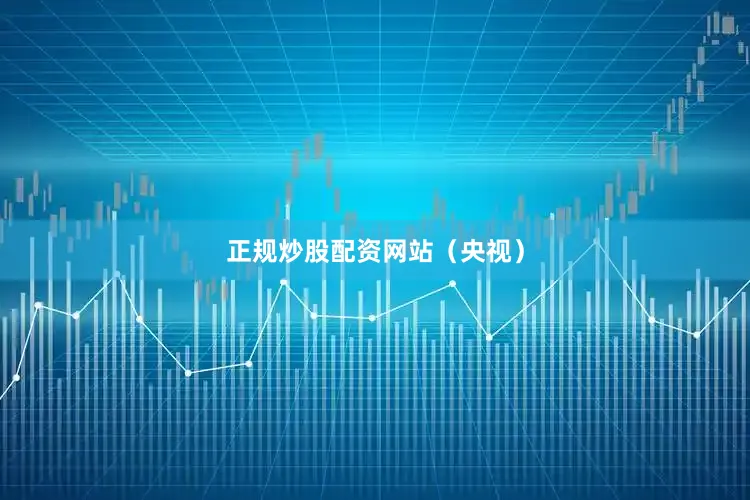站在这栋25层高的怪兽建筑脚下仰望,1200吨钛合金球悬挂在百米高空,反着冷光的金属表面映出整个东京湾。丹下健三1984年交出设计稿时,包工头差点把图纸当科幻小说扔出去——直径32米的球体要用巨型钢架吊在楼顶,侧面还得搭12米宽的超长阶梯。施工队边焊钢架边嘀咕:“电视台的人拍电视剧拍疯了吧?”
球体瞭望室里空调呼呼作响,技术员却常把温度调低。1200吨金属被太阳晒透后,室内变桑拿房,维修工戏称这是“会呼吸的巨型电饭煲”。财务部长每月看到电费单手就哆嗦:“半个东京的电都被这铁疙瘩吃了!”
但富士台就爱玩大的。1988年为庆生,他们把整列东方快车从欧洲运来。这古董火车在横滨码头靠岸时,海关人员捏着报关单犯愁:该填“节目道具”还是“钢铁废料”?列车开动那天,沿线居民举着饭团看稀奇,车厢里摄像机却对准香槟杯——制片人把庆功宴直接搬进移动片场。
彩色信号第一次从这栋楼发出是1964年9月。当时技术员蹲在球形控制室盯屏幕,满屏雪花突然蹦出彩条,全屋人跳起来撞到钛合金墙壁。七天后正式开播,转播车开去百货商场拍展示机,围观大爷指着彩色电视机吼:“这盒子会变戏法!”
球体下的制作中心像永动机。2004年某天凌晨三点,导播突然把带子摔桌上:“《救命病栋24小时》片尾医院镜头穿帮!”所有人扑向剪辑台返工,窗外大铁球浮在晨雾里像颗巨型安眠药。硬是靠着这股疯劲,他们连续八年霸着收视榜。木村拓哉2007年拍《华丽一族》时,电梯直通球体会议室改剧本。他对经纪人说:“在这开会,老觉得自己要被外星飞船吸走。”
楼下的停车场见证过更疯狂的事。1990年某日暴风雪,车队载着《东京爱情故事》剧组直奔机场。制片在车里吼着改完终稿,赤名莉香的毛衣在剧本上勾出线头。四年后《导盲犬小Q》拍幼犬戏份,训犬师抱着拉布拉多在钛合金球前合影,照片里狗狗仰头张嘴,活像要吞了这金属怪物。
25楼球体西侧的露台风最大。这里拍《最后的朋友》天台戏那天,工作人员用麻绳把锦户亮捆在栏杆上。演员被吹得鼻涕横流还得念台词,心里骂着“再高明的编剧也编不出这种罪”。那年观众看剧抹泪时,哪知道演员差点被风刮进太平洋。

F1引擎声曾在球体内引发共振。1989年日本大奖赛,解说员突然摘耳机嚷:“舒马赫撞车画面迟了三秒!”技术主管指着天花板上的球壁骂:“钛合金墙反射信号!”工程队连夜在球体西侧贴满吸音海绵,车迷后来听到的引擎轰鸣,都是从消音器里挤出来的假嗓。
吉祥物设计师肯定没爬上过球体顶层。当Kuramon的草图在会议室传阅时,晨间节目总监突然指向窗外:“你们设计的玩意儿像不像被压扁的铁球?”提案人反驳“这是前卫艺术”,女导播冷笑:“大妈们早上看到这个,牛奶都能喷成抽象画!”
呼号战争更显出这伙人有多倔。当初起名“中央电视台”被邮政省打回,业务员咬着笔杆瞎编出JOCX。报到一半自己都结巴:“这读着像打喷嚏!”员工偷懒缩写成CX,反倒印满了台庆纪念品,气得老台长拍铁皮墙:“小兔崽子们瞎改,这墙可是按毫米焊接的!”
当年被派去欧洲拆东方快车的员工,举着扳手对火车头发呆:“螺丝都锈死了!”最后整节车厢塞进货轮,随船工程师带了三箱零件。列车在神户港组装时,有个法国技工指着富士台大楼照片问:“你们电视台造火箭发射塔?”翻译憋着笑:“那是我们放咖啡杯的地方。”
如今球体瞭望台成了日剧最贵龙套。《昼颜》里主妇偷情在这里取景,《朝5晚9》里和尚表白也要爬百米楼梯。美术指导说:“反正每场戏拍到金属反光,观众就知道谁投资的。”清洁工最懂门道——他们总在周一擦掉玻璃上遗留的唇印,那都是周末剧组借景拍吻戏的战利品。
值班大爷锁闭顶楼时,总拿手电照照铁球底部。“听说这玩意儿能扛八级地震?”他伸手摸着冰凉的钛合金,忽然想到昨天重播《海螺小姐》的收视率。楼外街道上,《silent》的剧组正收起手语教学板,场记本封面粘着个CX贴纸。楼顶那个32米宽的金属球静悬在夜色中,倒映着东京璀璨的万家灯火。
股票查询网,股票配资门户推荐,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炒股配资资金以魔性笑声与活泼人设受到粉丝喜爱
- 下一篇:没有了